館藏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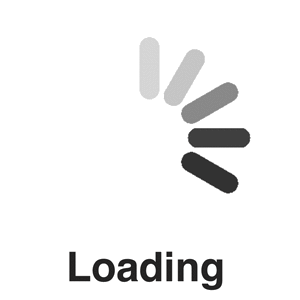
《品人明鏡──世說新語》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呢? 讀者若是拿這個問題去向專家學者請教,想必會得到類似以下的答案:《世說新語》一書,為南朝宋,劉義慶撰,有南朝梁,劉孝標的注,記載著自東漢末三個以迄晉、南朝宋間種種社會活動的實況,保存了此時期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社會科學諸方面之基礎資料。 若我們將眼光再加以伸延,探詢一下《世說新語》這本書在傳統歷史所佔有的地位,也不難發現以下的說辭:《世說新語》,談助之書也;《隋志》收入子部小說家類,與《燕丹子》《雜語》《要用語對》《辨林》等同列。這也就是說,傳統的中國人基本上是把《世說新語》看作是「聊天消遣」用的書。 前此這兩個對《世說新語》的界定,一個是這麼學究與乏味,另一個又是把它看得這麼「不正經」,似乎是「可有可無」的一部書(果真如此,現代的讀者,大可去從事另一種更有趣、更刺激的吳樂消遣,而不必去緊抱這樣一本似乎「過時」千年的古書),那麼何必還要佔用讀者寶貴人生的一部份來唸讀這本書呢? 所謂千里馬不遇伯樂,終與駑牛無異,偉大的作品之需有高明的讀者也是一樣的,我們且看民國以來最富贍詩人氣質的美學家宗白華是如何來看得《世說新語》這本書的: 這時代(指漢末魏晉六朝)以前──漢代──在藝術上過於質樸,在思想上定於一尊,統治於儒家;這時代以後──唐代──在藝術上過於成熟,在思想上又入於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這幾百年間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裡面的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同樣發揮到極致。 這也是中國周秦諸子以後第二個哲學時代,一些卓越的哲學天才──佛教的大師,也是生在這個時代……。 這晉人的美──是這全時代的最高峰──《世說新語》一書記述得挺生動,能以簡勁的筆墨畫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時代的色彩和空氣。文筆的簡約玄澹尤能傳神。(《美學散步.論世說新語和晉人之美》) 只有這一番界定,才算真正打開我們對《世說新語》的眼界;事實上,《世說新語》一書在中國文化史上所提供給後代炎黃子孫的,不啻是一次對華夏文化心理結構之大橫切面的檢視與觀照。整本書全從人類精神的平易切近處──日常生活──剖入,不著痕跡,不帶血絲,時時閃現出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式的銳利觀照的智慧光芒,與但丁神曲式的神聖詠歎的深遠情致。 《世說新語》,在心靈自由、眼界開放者的心目中,就是這樣一本教人念念不忘的書。 所以,讀者在面臨要不要讀本書時,至少獲得了一個最基本的保證──它絕對值得你為它每天花上幾分鐘的時間瞧一瞧,因為:第一,它敘說著讓人覺得再親近不過的故事,彷彿就曾發生在你身邊似的;第二,它所說的卻又不是讓人聽了就忘的故事,它所說的許多故事總是使人張大眼,屏住氣息,放穩脈搏,彷彿不如此,你就要錯失一次「認識自己」的千載難逢良機似的。它讓人覺得既熟悉又陌生。它讓人有想跟它「交談」的衝動。 《世說新語》,尤其對以下這幾類人有種擋不住的吸引力: 一、如果你是個喜歡觀人論品」的人,《世說新語》就是這樣一本為你而寫的書在要品評人物、認識人性之前,我們不妨誦讀尼采給人類的告誡:「我們這些認知者,是不被我們自己所知的…對於我們自己,我們不再是『知者』。」(《道德系譜學.序文I》) 不僅人性的形象因一再禁不起生活的考驗而粉碎,像莎翁筆下的哈姆雷特所引發調侃的那樣:「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得的傑作!……可是在我看來,這樣一個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麼?」(第二幕第二場)幾乎往往淪為「什麼也不是」的人性,究竟是什麼呢? 另一方面,就連人類深以為傲的那份精準無匹的認知能力,不也最後更在伊底帕斯王(古希臘世界中唯一解開獅身人面獸史芬克斯所給的謎題的人)身上發狂了嗎?人要解讀人性的謎,的確是不如想像中那樣容易的──謎底的週遭盡是等著將人吞噬的「瘋狂」。 那麼,我們擁有「認識人性,品評人物」這樣的機會嗎?如果有,這樣的機會又在哪裡可以覓得呢? 其實,日常生活裡,或是走在人來人往的大街時,或是在靜觀一張發黃的人相照片之際,我們的確都有過這樣的機會:在串乎有意與無意之間,我們忽爾看到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一個「我」的故事。知人責知心,而每個人的心不都明明白白地寫在他在臉上嗎? 一顆顆的心寫在一張張的臉上,但這一張張的臉又都是寫在哪裡呢?──寫在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上。 語言文字「說」著種種人性的故事:「美與醜、高貴與殘忍、聖潔與惡魔、靈悟與冥頑」都成文、現起於「語言文字的說話」中;離開語言文字的說話,人,非但不僅如尼采所說的那樣,「都是最遠離於他自己的」(《道德系譜學.序文I》),甚至只是「一個白癡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和騷動,卻找不到一丁點意義。」(《馬克白》第五幕第六場) 惟有肯虛心聆聽語言文字的說話的人,才越了主客對立的認知困境──人不再是遠離於他自己的;才解讀了自己的性情,別人的感受,人性的本質命運。 《世說新語》就是這樣一本好書:它紀錄人性,觀察人性,理解人性,同情人性,包容人性,然卻都是由劉義慶在虛心聆聽華夏民族的語言文字所道出的種種人性情境之中寫成的。 劉義慶從華夏民族之語言文字的說話中聽出了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歷「自新」「企羡」「傷逝」「棲逸」,到「尤悔」「紕漏」「惑溺」「仇隙」第三十六種人性的情境,也等於是聽出三十六種人性的面相,三十六種人物的品第。 劉義慶所道出的人物種種,完全是在虛靜的聆聽中現起的,讓人絲毫聽不到作者「創作的噪音」。這正是他比劉劭的《人物志》高明的地方:他不作知人理論的鋪陳,而只作情境的烘托與凸顯,無非就是要讀者也能跟他一樣,在虛心聆聽華夏民族的語言文字的說話中,知道人性是怎麼回事,認得人物是如何分等的。《世說新語》真正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含蓄品》)的好文字。 二、如果你是個「愛好智慧」的人,《世說新語》正是這樣一本為你而寫的書 魏晉的時代智慧,可從王羲之的詩句「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及「爭競非吾事,靜照在忘求」中看出其主要特徵。 這是一種接近尼采所謂「日神精神」的澄明觀照;說得更確切、更具象點,這種由「澄照群籟的虛懷」所組建充實起來的「智慧」,恰如秋天的日照,把寰宇間的事物萬象──管那麼參差不齊──都朗照得如此清晰、澄明,彷彿把天地萬物存在的意義全都跟我們挑明了似的。 我們若再追隨尼采的說法,而把「魏晉智慧」說成是「所有造型力量的神,代表規範、數量、界限和使一切野蠻感未開化的東西就範的力量」(參見《榮格文集》英文版╱卷六的<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一文),應該是不為過的。這也就是說,在魏晉智慧的朗照下,生命中的一切事物與存在──不管是現實的,還是可能的,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褪去事物身上原本抹不掉的渾沌與曖昧的氛圍。 在魏晉智慧的觀照下,一切存在都有了再清明不過的意義深度。 魏晉智慧有其極為具體、生動的呈現顯露,也有極其抽象的命題性提示。關於前者的呈現,陶淵明的詩是種典型;關於後者的提示,魏晉玄學則是最佳的說明。 且拿陶淵明的<時運>連篇詩來說吧!體現著魏晉智慧的詩人,不僅向外發現了「自然」的情韻,所謂: 山滌餘靄,宇曖微霄。 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詩人向內也發現到個人自己的生命情調。詩人唱得好: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 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在時間的「逝者如斯,不捨晝夜」當中,詩人更是意識到歷史的存在;他深遠地追想者往古的文化盛事: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 童冠齊業,閒詠以歸。 我愛其靜,寤寐交揮。 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最後,詩人乃至得以憑著時代特有的智慧之眼,看到一種人性的命運歸趨;陶淵明在<歸鳥>連篇詩中唱得令人動容: 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眼前的人世道路誠然悠遠,人性情愛的滋長、綿延卻是那樣表露無遺!) 在魏晉智慧看來,正是這樣的「一往深情」構成人性命運的歸宿。 魏晉這種表現在具體生活情境中的智慧澄照,有兩項特色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它在澄照自然、個人自己、歷史、人性命運的存在意義時所達到的明朗度,仍純是就存在的本體而非表象而言的。換言之,它真是一種尊重個性、物各付物的虛懷澄照;它繼承並開展了先秦道家的真理觀,它真的相信眼前這一切存在的根本依據,除了它們自己之外,再不可能是作何別的存在。 第二,它是一種能回到自己,為自己找到歸宿的智慧,因而跟西方精神現象中上那種以絕對自由為嚮往,以絕對毀滅為不可避免之宿命的「酒神精神」是大異其趣的。 魏晉智慧,在另一方面,也披露在高度抽象的命題性表述上。此一智慧的表現方式,就構成了中國思想史上所謂「魏晉玄學」的主調。 魏晉玄學的高峰發展,可以拿郭象的《莊子注》作代表。先前說過,魏晉智慧的「看」,乃是一種本體性的觀照與深詢;這有關存在本體的探詢,一旦把其中的情感抒發給抽離掉後,便是魏晉玄學的基本命題之所在。 魏晉智慧既是種物各付物、尊重個性的智慧,這種觀照向一旦轉化成玄學的命題,遂引生出郭象等人有關「有」「無」及「自生」觀念的構建與提出,他在《莊子.齊物論》的注中說: 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 姑且不論郭象在這裡對「有」「無」關係的主張恰當與否,單就他在本體論上所提出的「自生」這一觀念來說,「自生」就是「自有」。而「有」就只能是「自有」,至於「自有」意謂的就是「自己存在」。自己存在: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根據,除了它自己以外,再也無從找起;自己就是自己存在的終極根據。 郭象此一「本體論」的提法,對應於那高度看重「人格個性」與「隨興而行」的魏晉風流,不是挺合理的嗎? 事實上,郭象這種「物各有性,性各有極」、莫不「自有」的說法,正是魏晉洗鍊的智慧之眼──空潭瀉替,古鏡照神(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洗鍊品》)──的一番哲學性寫照。 三、如果你是個「嚮往深情」的人,《世說新語》更是為你寫的 魏晉風流中能有這樣一隻智慧之眼,不是沒有道理的。那個時代的文化天才,個個儘能把自然的韻致、自己的意向、歷史的脈動、與人性的命運看得如此透徹明白,為什麼?因為他們跟這種存在都是那麼「親近」。 華夏民族第一次這麼親近生命的本體! 這樣一個回答顯然不盡令人滿意。聰明的讀者馬上要追問:那使他們與其人生中一切存在走得如親近的「東西」──是一種生命的機制,也是一種本體存在的條件──又是什麼呢? 讀者若還記得前此所提那做為魏晉智慧之命運歸趨的「深情」,相信便已知道答案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沒錯,就是一往情深的「深情」,就是由魏晉深情拉近那個時代中的文化天才與自然韻致、歷史脈動與人性命運的距離的:魏晉智慧,原來就是在深情的人生泥土中綻放出來的朵璀璨感人的人性奇葩! 魏晉的深情,最主要還是源於那個時代的文化天才,是那麼熱中於與那無所不包而又真實無偽的「自己」(亦即生命本體;王弼的「無」說的就是這樣的「自己」)親近。只有那能「與自己親近」的人,才稱得上是深情種子。 一往情深,就是時時不忘與自己親近,或透過對自然的欣賞,或透過對人物的品評,或透過對歷史的緬想。 魏晉深情的緣起,自也有其歷史契機:華夏文化剛擺脫掉先秦以前那種講究群體情感的喚起與鞏固的框架符號,而孔子「仁者的生活世界」在未得到完整與具體的落實與發揚前,歷史的巨輪早已無情地滾入兩漢的「小人儒社會」;華夏文化在經過東漢中葉以後一場場的動亂與戰爭後,步入魏晉,藉著戰爭動亂所帶來的精神鬆綁,終於有機會將自秦漢以來長久積累在體內的庸俗主義、妥協主義、符號主義排泄殆盡,進而能上接先秦諸子的遺風餘韻,再度「回到自己」「與自己親近」──魏晉深情於焉誕生! 四、如果你是「愛美」的人,《世說新語》絕對是為你寫的 華夏民族的生命存在,歷經夏夜的暴風雨之後,在一個秋日澄照的清晨醒來,發現它置身於其中的生活世界,在一夕之間突然變得那麼可親可近而又無不美好。 人物是美的。 和嶠「森森如千丈松」(賞舉.15),王衍「神姿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賞譽.16)嵇康「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得引」(容止.5)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容止.26),王右軍「飄若遊雲,矯若驚龍」(容止.30),無一不是飽含深度之美的人物。 深情是美的。 王戎千古自詡語「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傷逝4),衛玠「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言語.32),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安因稱他是「一往有深情」(任誕.42)講的都是這種「終當為情死」(任誕.54)屈騷式的深情之美。 言語是美的。 有人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有人論史漢,靡靡可聽;有人說夙昔典型,也是超超玄著(言語),大珠小珠落玉盤,擲地須作金石聲,讓「聆聽」不僅是領受真理的法門,更成其為人生最高妙的美感享受。德音迴盪,妙語流連,千載之下,猶聞其聲。 自然山水是美的。 近物如簡文入華林園對左右說:「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言語.61),遠景如顧愷之形容會稽山川之美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言語.88),都是有自由的心靈才有福消受的天地大美。 心靈是美的。 阮光祿有好車,有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阮後來知道這事,感歎道:「吾有車而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德行.32);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德行.34);嵇康「臨形東市,神氣不娭,索琴彈之,奏廣陵散」(雅量.2),不惜性命將休,但歎此曲絕矣:映入吾人心目中的是種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杳然自得、超然物外的心靈之美;康德所謂「美是道德的象徵」(《判斷力批判》第59節),不就是專為這種美而說的嗎? 五、如果你是「愛聽故事」的人,《世說新語》全是為你寫的 什麼時候聽故事最好? 1.瘟疫來臨時──一三四八年,一場令人怵目驚心的瘟疫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肆虐開來。在一個清晨裡,三個年輕男士及七位年輕貴婦在一所教堂外邂逅,其中一人便提議逃離瘟疫猖獗的城市,逍遙餘生去。十人當即贊成此議,翌日,一行就躲到城郊外的一座別墅裡去。在那裡,他們輪流講故事,自娛娛人。這就是薄伽邱《十日談》的由來。 2.異族入主時──蒙古鐵騎壓境,入主中原,造成華夏民族第一次徹底的亡國。當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讀書人但能以言談互娛互慰,度此漫漫長夜。「吾友來亦不便飲酒,欽飲則飲,欲止先止,各隨其心,不以酒為樂,以談為樂也」(水滸傳.序)),於是便說了媲美《史記》《離騷》的《水滸傳》。 3.朋友交心、促膝而談時──晉人對友誼的重視,培養成功一種高級的社交文化(「竹林之遊」「蘭亭禊集」「洛水之戲」「新亭卉宴」等)。玄理的辯論和人物的品藻是這社交的主要內容。因此談吐措詞的雋妙,空前絕後。晉人書札和小品文中雋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淵明的詩句和文句的雋妙,也是這時代的產物。(《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之美》) 孔子說的「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這樣具體實現魏晉人的「說故事」與「聽故事」之中。《世說新語》正是這種「樂」的完美結晶,玲瓏剔透,包羅萬象。 《世說新語》既是一本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都以絕妙好辭訴說著種種人故事的書,讀者自然不必一本正經,大可乘興開卷,盡興閤書,隨與領會。因為,書中的每一則故事幾乎都是契入魏晉風流而又引人入勝的最佳切入點。 抱著聽故事的心情讀此書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就只是聽故事,什麼都不求,然而就在那一無所求的聆聽中,當他們渾然忘我地聽到故事的結尾時,他們恍然聽到是又一個嶄新的時代風貌與生命形態的誕生。 就像《十日談》將中世紀的幻影、神祕、恐怖與恍惚都一併逐出藝術神殿之外而為文藝復興吹響劃時代的號角一樣,《世說新語》也在一則又一則的故事間總結魏晉那個時代的美與醜,超脫與滯障,道德與不義,進而為接踵而來的盛唐之音奠定深遠、閎大而靈秀的生命基調。 我(筆者)是這樣讀《世說新語》的: 我跟所有愛讀書的人一樣,是個聆聽者,不是個作者。 我試著去聆聽《世說新語》對我們這個時代都說了些什麼。在這當中,如果我錯失了些什麼,或誤解了些什麼,那只能我自己不夠虛心與沉靜,不是個好的聆聽者。 但是這種情形實也凸顯出同樣身為聆聽者的你的重要性:你的包容、想像、理解與批判,正足以彌補我的不夠虛心。 如果我有幸、當真也聆聽到一些《世說新語》不吝對我們這個時代吐露旳靡靡絮語,乃至引發你的共鳴,這仍都歸功於《世說新語》的文字實在好。因為,做為生來就是說漢語、寫漢字的我,日日明月浸淫在華夏民族的語言文字氛圍之中,猶如魚優游於江湖之中,鳥高翔於大氣之中,畢竟只是個聆聽者,而且一向是,未來也將一直是。